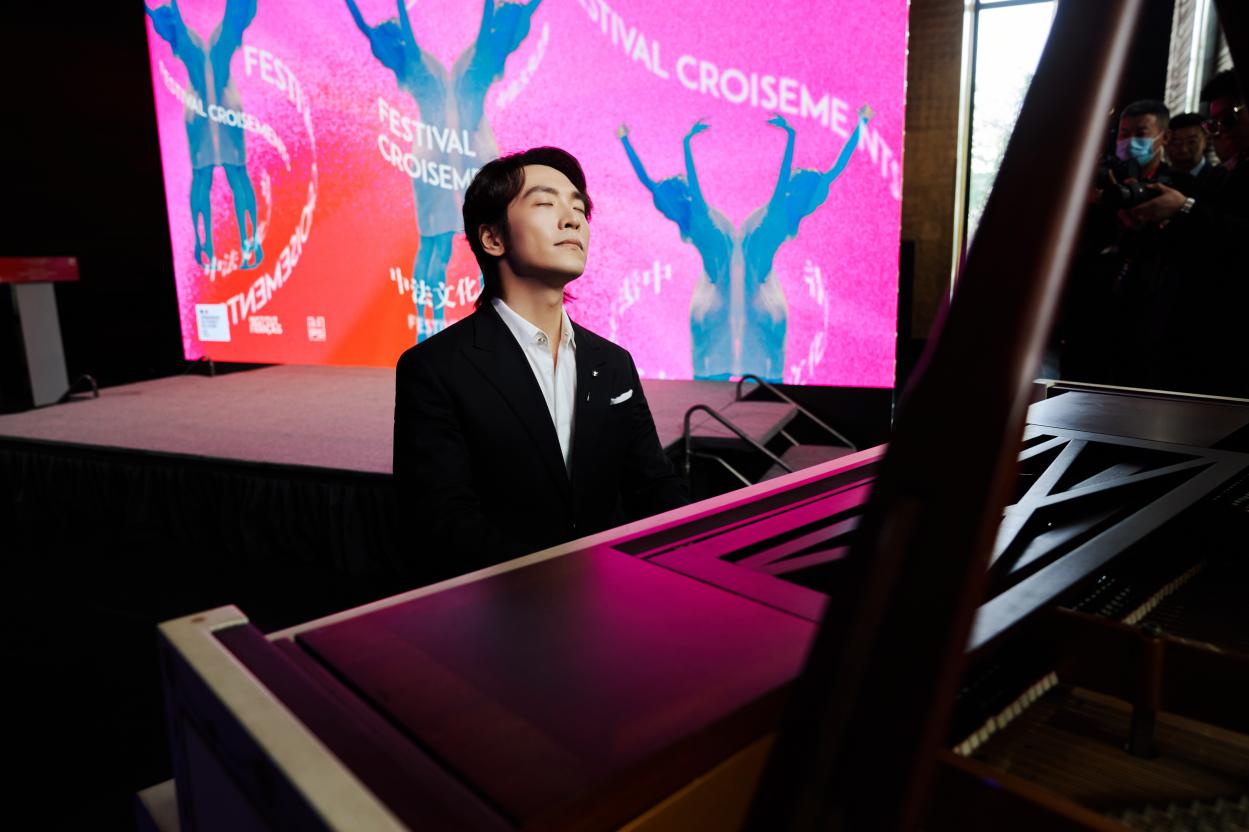- 恒瑞医药张连山博士对话中科院院士 畅谈中国医药创新之路
- 2021年03月26日来源:恒瑞医药
提要: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2021EBC)前不久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开幕式上恒瑞医药高级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博士对话中国科学院陈凯先院士,围绕“中国医药创新之路径”深入展开,引发行业共鸣,现场掌声连连。
第六届易贸生物产业大会暨易贸生物产业展览(2021EBC)前不久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开幕式上恒瑞医药高级副总经理兼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博士对话中国科学院陈凯先院士,围绕“中国医药创新之路径”深入展开,引发行业共鸣,现场掌声连连。
根据会议速记将现场精彩对话整编如下:
张连山博士:特别高兴在大会上看到这么多同事和同行,今天有机会请到陈凯先院士来一起做工业和学术界的对话,展开一次碰撞和交流。有幸与陈院士结识于2010年,俗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充分认识到中国医药行业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与陈院士辛勤的努力息息相关。那么,下面请陈院士做下自我介绍。
陈凯先院士:各位同道、各位专家、来宾大家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个会议,和大家一起做交流和探讨。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我从事药物研究几十年,主要研究领域是药物化学和药物分子设计,也参加了一些药物的发现、研究和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同事和同行的支持与帮助,非常感谢(大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我也参与了国家推动的重大系列药物的研发计划,包括重大科技专项,深有感悟,在此,很开心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对“创新”的理解
张连山博士:“创新”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也是一个“Rewarding Process”。
陈凯先院士:“创新”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新突破,这是我们追求的创新。创新是我们国家各个领域,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医药创新之路径
张连山博士:我来自江苏恒瑞,主要负责公司的研发。在加入恒瑞之前,一直在国外,经过几十年的训练和工作(后回国),非常高兴能参与和见证中国最近十年生物医药创新的过程,也受到过像陈院士等一些中国专家的指导。最近有很多讨论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做真正意义上的“first in class”,以及目前我们正处于什么阶段?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fast follow on”的过程中,慢慢要进入“first in class”。做“first in class”需要源头上的创新,实际上这更依赖于基础研究。陈院士您一直在基础研究领域,请您给同行提些建议?
陈凯先院士:连山,你提的问题重要且及时。我国生物医药经历建国七十年来的逐步探索,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此,用几句话回顾一下中国生物医药发展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药物研发能力还非常薄弱,主要依靠向国外仿制。国外有一个新药研发成功,国内就仿制,以此来支撑我们产业的发展,也支撑了医院用药、临床医疗。在这四十多年中,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创新成果,也有像青蒿素这样影响巨大的成果。但总体而言,我们研究的创新药很少,研究的能力薄弱,在国际上还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至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以仿制为主的阶段”。
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生物医药创新能力有了极大提升。在2008年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支持组织引导下,我国药物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从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在重大专项支持之下,获批上市的一类新药有50多个;2018年我国批准上市的一类新药有9个;2019年自主研发批准上市的新药12个;2020年是15个。我们一年能够研发十多个具有新的化学结构和新化学实体的药物,这是巨大的进步。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又处在什么水平呢?现在全世界一年产生的新化学实体药物约几十个,多的年份五六十个、六七十个,少的年份二三十个、三四十个。在这样的格局中,中国一年研发十多个,这说明我们的创新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模仿创新的阶段”。
为什么叫模仿创新呢?因为药的化学结构是新的,有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但它所依据的作用机制、作用靶点还是国外首先发现的,并不是我们首先发现和首创的。这个研究方向还是国外首先开创,我们跟在后面用自己知识产权做了新药。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还不够,这个阶段我们叫做“me too/me better”。
“fast follow”我们把它叫做模仿式创新,这个阶段很重要,但我们仍觉察到现今发展所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刚才连山总裁讲的,怎么在原创新药“first in class”这个方面做出成果,引领新的发展方向。这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仍相当薄弱。所以连山总裁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认准今天达到的新高度;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短板和不足,怎么面对未来进一步的发展?从现在开始展望未来,我们要开辟一个新阶段——“原创研究的阶段”,我们不仅能在现有靶点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做药,还要能够开创新的靶点、新的作用机制,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我们和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
怎么来发现一个新的靶点,发现一个药物治疗的新作用机制?目前来看,这方面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比较空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药物创新体系。我认为要高度重视药物作用的新靶点、新机制、新技术、新策略、新方法的创新。在过去创新的基础上提升一步,这和技术研究相关。我们能感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推动我国基础性研究,助力在原创方面有更多发现、创造、创新。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现在我国的科技投入约占GDP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几,这个数值不算很高,但大体也说得过去。问题是我们用在基础研究的部分只占这个数值的5%,占比相当低,发达国家用于基础研究的份额大概占到百分之十几,高的接近百分之二十,所以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同时要不断增加这方面的投入。资料显示,2011年全球有17个突破性研发药物,能找到15篇与之相关的基础研究论文,这直接奠定了这些新药发现的基础。这非常有利地说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基础研究)可以开辟我们药物研究的新突破口和新方向。
另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研究向应用的转化,其实近几年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还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每年在CNS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新的作用机制和靶点(潜在成果的发现)。但要把它转化成药物研究的靶点并确认,在研究方面的衔接仍然不够。所以要加强对技术研究的重视和投入,更进一步完善药物创新体系,使它能够向上游适当的延伸,另外一方面要努力促进基础研究的成果向药物研究的靶点作用机制这方面转化。
张连山博士:陈院士说得非常到位,实际上新药创新跟其他创新一模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过去做仿制药也是这样,不要以为做仿制药简单,实际上这里面也有很多创新的过程。通过做仿制药和模仿创新,生产的新药解决了中国患者基础用药的问题,包括PD-1在内,正在服务于中国广大患者。我认为在重大专项实施的过程中,已经把中国做药的整个结构打造出来了。再加上现有技术平台,不管是国内本土的,还是海归回国后进一步打造的技术平台,都已经很成熟了。下一步就像您说的,怎么才能把中国研究者做出来的“生物发现”、“可能成为一个药物靶点的发现”变成能解决未满足临床需求(的药物),这也是在座各位都应去思考的。
我们在上海、北京做这件事情,跟过去重大专项那个时期做的事情不一样。现在要更注重前沿的投入(从国家层面)。当然从企业层面也要跟科研院所进行一些合作,就是说转化过程(研究)。之前您已经讲过了,其实就是在一个转化过程当中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如何与医院的临床研究结合起来?很多在座的都是我的同行,都是做分子的。一个分子有效性做出来,安全性做出来,这也只是在动物层面,其实真正在临床上把精准患者人群找出来,把它做成可以上市的药,还需要很多医院的医生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您有些哪些思考,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凯先院士:最近一二十年,可以说中国生物医药研究和产业变化大,发展速度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亲身经历很多,也加深了很多认识。过去我是一名在研究所、实验室和高校工作的科技人员,认识还比较狭隘。我们认为药物先在研究单位研究成功了,然后拿到医院去实验,再拿到医院去用。其实临床的研究、医院的研究对于药物的研发起到非常深刻、重大的作用,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是不足的。最近十年,对这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想这跟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发展潮流,及其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本世纪以来提出的转化医学研究理念和模式、还有像精准医学方面的研究思路等等。转化医学也好,精准医学也好,这些理念都是从临床的实践中,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转化医学重视临床的需求、发现以及观察到的现象,以此来牵引、指导基础研究,这样一来,研究成果也能快速应用到临床。李院长的报告是非常好的转化医学研究实例,把临床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临床中所用的样本、指标、数据,用来牵引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指导研究工作。这反映了临床研究对整个研究工作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很多药物的研究都离不开临床研究的指导和支持。
然而,目前我国临床研究能力、规模和发展之间仍存在很多不适应的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已在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建立了一些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我想这个对于加强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交流,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连山博士:我们要做原创的东西,西方的好多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的。很多海外生物公司,是由大学的教授或医生成立的,我想不远的将来在中国也会看到。一方面转化医学对我们整个行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推动转化研究的人才也很重要。陈院士您也带过很多学生,也给中国整个行业培养了很多人才,(在这方面)您有哪些想法,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凯先院士:好,大家都说创新重要,中国过去十多年生物医药的发展有了巨大进步,用一句话概括是创新创造了这样的改革。过去十多年创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生物医药发展格局,人才是这背后最重要的核心因素。像连山一样,回国推动生物医药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常常在报告中讲,过去十多年我国生物医药发展的标志性现象就是一批海归学者回国把创新和创业结合起来。他们是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支战略性队伍。这也给人才的培养带来两点重要启发:一是我们要在当今生命科学发展的背景之下,树立多学科交叉的理念,培养有宽广视野和知识背景且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的人才。
我是从药物化学专业出来的,药物化学的教材、药物化学的研究生培养,也越来越突破传统理念。(药物化学)会跟生命科学、药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有非常密切的交叉。现在很多国外编的高等药物化学的教材、医学教科书,已经跟传统的药物化学大不一样。它结合了一个药物发现的过程,综合性讲述多学科知识,这对我们是一个启发。培养人才,要尽可能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有多学科交叉的背景。
我觉得这还不够,像连山这样,海外归来创业、创新很成功的人士。他们不光拥有知识背景,而且还需要懂得怎么组织、运作和领导一个项目的论证、推进,并且还拥有和企业、资本市场互动的丰富经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动药物研发、推动企业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综合性要求。今后要能够培养更多推动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综合性人才。很多海归人才在国外大药企工作时,不仅做研发还担任申报新药等多项工作职能。今后培养的人才要努力适应实际需要。
张连山博士:谢谢陈院士,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中国新药创新之所以在过去十年迅猛发展,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新药创新黄金时代”,和大批海归人才,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以及在座各位辛勤的努力密切相关。让我们继续努力、不断学习,把新药创新做好!因为还有很多患者在等我们生产的新药,谢谢大家!